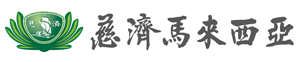城市的灯火再璀璨,也照不进每一处孤单的角落。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,仍有一群人默默地活在边缘,他们是城市中最不被看见的存在——街友。
街友,并不只是无家可归那么简单。他们或许是出狱后无处可归的长者、或是父母往生后与手足失联的单身者、也有年仅十多岁,因家庭破裂而逃离甘榜的孩子。有人因贫病、有人因失业顿失依靠,也有人只是因为一场误解,就与家失之交臂。他们并不是社会的负担,而是尚未被好好接住的生命碎片。


◎生命的教育 不在课堂里
2025年7月6日,慈济雪隆分会大中慈少进阶班的学生,亲手筹备了一场温暖的行动。他们从采买食材、备料、烹煮到打包,合力准备了两百五十份素食便当,亲自送往美丹端姑流浪者转型中心,为街友送上一餐温饱,更带去一分真诚的关怀与陪伴。活动中不只是物资的给予,还有剪发、绘画、陪伴、手语表演等活动,让这一场送爱行动,成为一堂别具意义的生命教育课。
“我原本以为街友就是流浪汉,态度恶劣,可能还会抢东西。”慈少生廖康和坦言,来之前对街友有着既定印象,“可是真正接触之后才发现,他们其实跟我们没什么不同,有礼貌也亲切,根本没有想像中的可怕。”
他记得,一位牙齿掉光的老奶奶接过便当后深深一鞠躬说“谢谢”,那一幕令他心头一震。 “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在太阳底下流的每一滴汗,都值得了。”
当天清晨九点半,慈少生们便在USJ共修处展开备餐工作:洗菜、切菜、炸素叉烧、煮饭、打包……整个早上忙得不可开交。虽然天气酷热,有遮阳伞也挡不住高温,大家仍然坚持不懈。


慈少生黄紫恩平日课业繁重,身体又不适,但仍主动参与,“很累,但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有意义活动。”她笑着说:“切红萝卜切到手都红了啦!”
紫恩回忆,自己从三岁就跟随慈济妈妈当小志工,一路走来的慈济路,说道:“我去过孤儿院、老人院,也去过智障中心,这是我第一次走上街头送爱。每次的活动都让我学到不一样的东西,是很宝贵的人生体验。”
身形瘦小的陈奕霖双手紧握锅铲,不停地翻炒锅中的食材。虽然不是第一次下厨,但这却是他第一次为这么多人掌勺。一锅菜,肩上却背着沉甸甸的责任,压力从调味开始蔓延——盐放得够吗?酱油会不会太淡?他说:“一点点的失误,就可能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遗憾。”
他不敢松懈,全神贯注地翻炒着,让锅中的蔬食如浪花般翻涌,只为让这一道菜色香味俱全,为街友送上最有诚意的一餐。 “现在双肩真的很痛,但我只想把这份爱的力量煮进每一口饭菜里。”


◎六毛钱的捐款 一份无声感动
午后五时,美丹端姑流浪者转型中心人潮逐渐聚集。志工黄晓清(虑晓)身影穿梭其中,蹲下身子、轻声细语地与街友交谈。她的眼神没有距离,动作没有优越,像对待一位老朋友。
“不是每一位前来领便当的人都是为了贪小便宜,更多时候,他们是带着仅存的尊严走来。”晓清指出,许多街友其实渴望自立,也愿意敞开心扉分享故事,甚至默默成为慈济的捐款者。 “我们曾统计过,有多达两百四十位街友悄悄捐款,因为他们不想永远只是接受帮助的人。”
这项街友关怀行动,起初只是一小群志工,延续英文组举办的年度关怀活动。从中央艺术坊( Centre Market )街角面对场地纠纷与警察驱赶问题,到今天稳定落脚于美丹端姑流浪者转型中心。三年来,志工们经历重重挑战,也收获了更多感动。
“感动真的太多了,讲都讲不完。”黄晓清语调轻轻分享一段感动时刻。原本关怀活动是每两周一次,但去年为了配合马来西亚日( 9月16日)街头特别多了些人潮,志工们便与其他非营利组织协调,再次出队。当她提前告知街友:“我们会在9月16日那天再来。”一位熟识的女街友先是开心点头,却旋即又露出迟疑的神情。
“我很开心,也很不开心。”那位街友说。黄晓清一愣:“为什么?” 街友声音微弱说:“开心,是因为你们会来,我真的很欢喜。但我也很担心……担心那天我没有钱可以捐款。我平时都是靠讨钱,一天最多只能凑到几毛钱……我怕一毛都筹不到来做捐款。”
黄晓清回忆起那一刻,眼泪不争气地涌了出来。她说:“她们虽然一无所有,却仍旧想布施——因为她们不愿永远是接受的一方。即使手中只握着微薄的钱币,也渴望翻转手心,成为那个手心向下的人。”
一枚硬币,可能微不足道,却承载着一份对尊严的渴望。正如证严上人开示:“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,而是有心人的参与”。这一群流离失所的人们,在志工的陪伴下,选择了付出,书写出手心向下的勇气。他们,不是值得可怜的对象,而是活出尊严的见证者。


◎关怀与陪伴中 重拾一份尊严
这天的活动也设有理发服务。人群中,一位身形清瘦、衣着整洁的中年男子安静坐着。他刚剪完头发,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,语气谦和文雅。他叫肯尼夫( Kenneth Matthews ),在街头漂泊已七个月。
过去,他也曾拥有平凡生活——有妻子、有女儿、有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。直到那场错误,他不愿详谈的往事,如石子击破了家庭的平静。妻女无法原谅他,激烈的争吵成为家中日常,最终,他选择离开。
两个月后,他试图回家,想弥补,想重来,却发现家门已不再为他敞开。尤其是女儿,那双曾经信赖的眼,如今冷漠如霜。肯尼夫说: “她的情绪太激烈了,我没办法留下。”于是他成了一名街友,在城市边缘过日子。
“我每天都在找临工,也会来这里排队洗澡、领便当。”他说:“不是我不努力,只是,有些事,不是努力就能解决的。”那句话里,有无奈,也有难言的愧疚。这世上,有些流浪,不是因为懒惰,而是因为人生的裂缝太深,暂时还找不到缝补的方法。
尽管困于街头,他仍尽力维持与家庭的连结: “我会用政府的补助金,请人帮我买东西,再转交给太太。虽然回不了家,但我还想尽点责任。 ”语毕,他低头沉默片刻,轻声补上一句: “希望有一天会有奇迹,我能真正回家。 ”
生活不易,但他仍选择付出。每逢星期五,肯尼夫会在穆斯林做礼拜时乞讨,那是他仅有的收入来源。 “那天我收集到的钱,我捐出一部分,交给慈济志工。 ”他说着: “你们让我们觉得被尊重。和其他团体不同,慈济人讲话有礼貌,也成熟,让我们觉得很自在。穆斯林朋友们也这么觉得,大家都喜欢你们来。 ”
肯尼夫特别感谢志工提供的理发服务,称赞志工温柔又细心,更对慈少生赞不绝口: “这群少年真的很有礼貌、很亲切。看见他们的言行举止,就知道你们教育得很好。”
街头的风依旧,肯尼夫的故事,为这个午后添上一份深沉的温柔。他或许还在等一个“回家”的时刻,但他早已在慈济志工的陪伴下,拾回生命里那份被理解的尊严。

●
城市从不完美,但人心可以让它温暖。慈少班的这场街友送爱行动,是一堂无可取代的生命教育课。让孩子学习用眼睛看见、用双手行动、用心灵感受,也让参与者再次明白——哪怕是一份便当,也能是让人感受到温暖。正如上人所言:“有心,就有福;付出,就是富。”这一天,慈少孩子与父母,让吉隆坡的街头,有了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光。